佐赫蘭‧馬姆達尼對印度政治論述有何啟示
薩拉尤·帕尼
雖然地球另一端城市的市長選舉可能對印度人的生活影響不大,但印度人對印度僑民的看法,卻總能讓我們窺見印度主流觀念。佐赫蘭·馬姆達尼在紐約市長競選中令人震驚的民主黨初選中獲勝,以及印度國內對此的反應,引出了一個始終處於印度政治話語核心的問題:當我們剝奪公民身份的合法性時,誰是印度人,又由誰來定義“印度人”的真正含義。
莫迪在其多次出訪中,將與印度教僑民的互動作為其外交政策的核心要素。在印度人民黨的框架下,印度教僑民是唯一真正與印度政策利益相關的印度僑民群體。穆斯林僑民普遍被從論述中抹去,而錫克教僑民則被積極妖魔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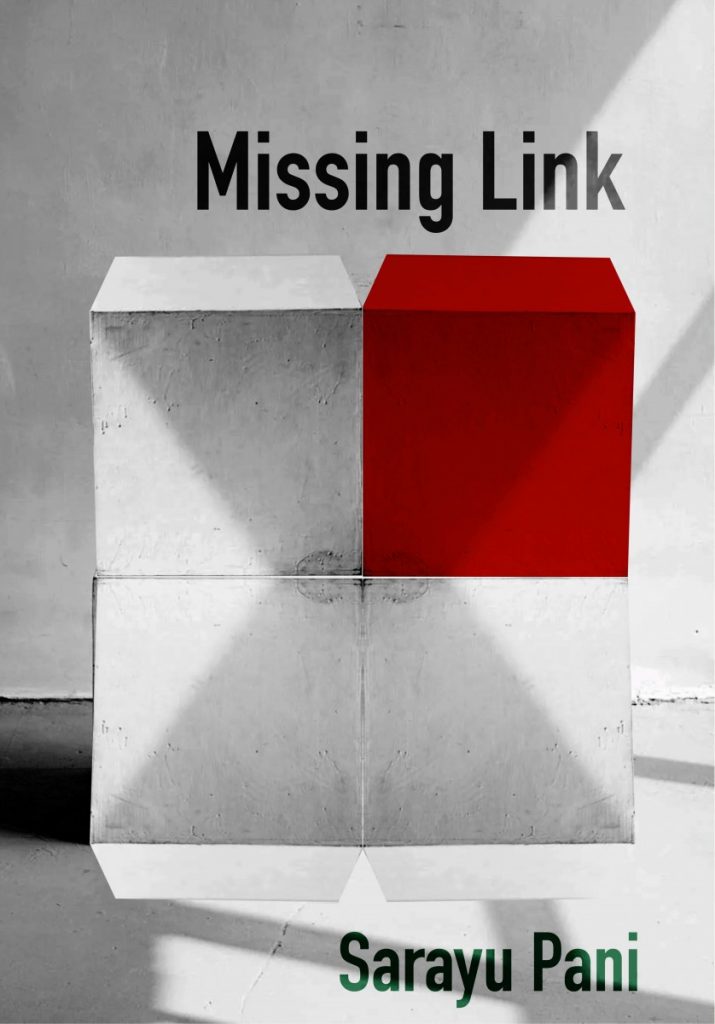 過去十年,媒體普遍以此為線索。包括里希·蘇納克、桑達爾·皮查伊甚至烏莎·萬斯在內的印度教僑民在印度都受到媒體的廣泛關注,媒體普遍強調他們與印度的聯繫。但對印度穆斯林來說,放棄合法公民身分似乎切斷了他們在印度公眾心目中與印度的文化聯繫。例如,費雷德·扎卡里亞、邁赫迪·哈桑和哈桑·明哈吉等美國公眾人物,他們的父母也都出生在印度,因此他們通常被更籠統地描述為南亞裔。
過去十年,媒體普遍以此為線索。包括里希·蘇納克、桑達爾·皮查伊甚至烏莎·萬斯在內的印度教僑民在印度都受到媒體的廣泛關注,媒體普遍強調他們與印度的聯繫。但對印度穆斯林來說,放棄合法公民身分似乎切斷了他們在印度公眾心目中與印度的文化聯繫。例如,費雷德·扎卡里亞、邁赫迪·哈桑和哈桑·明哈吉等美國公眾人物,他們的父母也都出生在印度,因此他們通常被更籠統地描述為南亞裔。
雖然莫迪執政期間無疑加劇了這些分歧,但要真正解釋這一現象,我們需要探討印度獨立前自由派菁英所設想的世俗主義中固有的悖論。
例如,印度國民大會黨1931年在卡拉奇通過的決議,規定了成年人的普選權、國家對所有宗教的中立、宗教自由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後來憲法中規定的一些基本權利正是以此為藍本。同時,在文化層面,一個獨特的印度教國家形像也正在形成。
蘇瑪蒂·拉馬斯瓦米(Sumathy Ramaswamy)的作品追溯了印度女神(Bharat Mata)作為國家神靈的形象演變,為這一現象提供了有趣的視角。儘管早期的印度女神形象靈感源自不列顛尼亞等其他女性形式的領土形象,但到了20世紀30年代,印度女神的視覺標準逐漸形成,其形象與疊加在印度地圖上的印度教女神形象極為相似。
到了20世紀40年代,在一些版本中出現了她手持三叉戟的形象。這種文化意象營造出一種印象,即一個國家本質上永遠是印度教國家。國大黨許多堅定的世俗國家支持者並不反對這種框架,即該國的文化代表本質上是印度教(通常是高種姓),而該國在法律上仍然是世俗的。

印度拉達克蒂克西印度陸軍基地門口的巴拉特·瑪塔(印度母親)雕像。照片:John Hill,CC BY-SA 4.0 來自 Wikimedia Commons
不出所料,這為後殖民時代穆斯林流行文化從印度公共領域中消失奠定了基礎,而這一進程在莫迪執政時期更是急劇加速。從寶萊塢穆斯林社交圈的消亡,到城鎮改名以抹去其與莫臥兒王朝的聯繫,印度性概念的主導性想像日益且完全地轉向了印度教。
多年來,這導致了一種社會環境的僵化,即使在世俗的印度話語體系中,印度教徒在法律和文化上都被視為印度人,而穆斯林則僅在法律權利上被視為印度人。例如,近年來針對莫迪印度教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反對力量,也選擇將焦點集中在印度憲法賦予少數群體的合法權利上,而迴避了諸如印度莫臥兒王朝統治被歷史抹殺等問題。
由此產生的必然結果是,在公開討論中,如果僑民不再受印度公民身份的法律約束,那麼如果他們是印度教徒,則可以保留他們的印度文化特徵,但如果他們是穆斯林,則不能。
印度媒體是否選擇將馬姆達尼或其他僑民視為印度人,當然通常與僑民本身無關。然而,這場關於誰是或不是印度人的文化爭論,在印度國內有著更深遠的影響。
另請閱讀:印度為何錯過了佐赫蘭·馬姆達尼的故事?
自印度獨立以來,印度穆斯林文化一直被排除在印度性定義之外,這意味著,儘管印度穆斯林在技術上享有完全的法律平等,但他們仍然被迫允許其在國家政體中的文化空間受到印度教多數派的影響。
對於自由派印度教菁英來說,印度穆斯林常常被貶低為一個釘子,他們的存在證實了自由派將印度視為世俗國家,也證實了「上層」種姓的自由派相信印度教是一種獨特寬容的信仰(前提是這些穆斯林迴避自身信仰中更明顯的標誌,並反覆宣稱其民族認同高於宗教認同)。對於印度民族主義者來說,印度穆斯林是一個永久的威脅性“他者”,他們的印度教民族敘事可以圍繞著這個“他者”來塑造。印度穆斯林試圖掌控自己的身份並在這些框架之外定義自己在國家政體中的角色的任何嘗試都很少得到支持。尤其能說明問題的是,這一代最具魅力的一些印度年輕穆斯林因其在《公民身份修正法》抗議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而仍然身陷囹圄。
有趣的是,印度穆斯林也對這些印度教的印度性框架做出了貢獻。在梅赫布汗 1957 年的史詩《印度母親》中,納爾吉斯的角色拉達(名義上的印度母親)作為新解放的印度人民價值觀的隱喻,而村莊作為後殖民時期印度的隱喻,都是明顯的印度教人物。在長達四十年的職業生涯中,寶萊塢巨星沙魯克汗只在少數電影中扮演穆斯林角色。其中一部是電影《Chak De! India》中的曲棍球教練卡比爾汗,該角色更多地強化而不是挑戰了這樣一種觀點,即印度穆斯林的印度性最終取決於他的印度教鄰居的眼光,對於印度穆斯林來說,在自己的祖國獲得認可是必須通過努力才能實現的。

沙魯克汗在《Chak De!》中印度'。
印度特性的文化概念和公民身分的合法性之間的分離從來都不是無懈可擊的。這些文化定義常常會蔓延到法律領域。例如,1947 年 12 月關於找回被綁架婦女的跨自治領條約規定,在分治期間被綁架並與其他宗教的男子一起生活的婦女必須被送回她們的家中(必要時可以違背她們的意願)。在已成為巴基斯坦一部分的地區找回的印度教和錫克教婦女的家被推定為印度,即使她們中的許多人以前從未踏足過那裡,也沒有家人願意接收她們。儘管印度自認為是一個世俗國家,但它也沒有為在邊境這一側與印度教和錫克教男子一起生活的穆斯林婦女提供任何選擇。她們被找回並遣返回巴基斯坦,有時甚至是違背她們的意願。
2019 年《公民身份修正法》的頒布,以及最近在古吉拉特邦和馬哈拉施特拉邦逮捕和驅逐來自西孟加拉邦的穆斯林移民工人的一系列事件,警方在沒有任何司法程序或監督的情況下稱他們為孟加拉人,並將他們驅逐出境進入孟加拉國,再次強調了民族的宗教和文化觀念可以多麼迅速地凌駕於世俗公民身份的法律保障之上。
佐赫蘭·馬姆達尼自稱是南亞裔,印度公眾輿論很難將他定型。他的母親、電影製片人米拉奈爾是印度裔印度教徒,電影在印度家喻戶曉,廣受好評。奈爾 1988 年拍攝的印地語電影《平安孟買》榮獲印度第三高平民榮譽——蓮花士勳章,並代表印度角逐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馬姆達尼極具魅力的競選廣告,點綴著寶萊塢風格、對話和音樂,也完美地打動了媒體的心弦。另一方面,馬姆達尼對莫迪和巴布里清真寺的直言不諱,以及他總體上不願承認或遵守印度穆斯林在世俗空間中被設定的狹隘話語界限,也引起了自由派的憤怒。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公開宣稱世俗化的國大黨發言人阿布舍克·馬努·辛格維 (Abhishek Manu Singhvi) 本能地用幾代以來用來懲戒偏離路線的印度穆斯林和其他少數民族的語言來批評馬姆達尼 — —指責他們為巴基斯坦的利益服務。
且不論馬姆達尼的立場或候選人資格如何,重要的是要承認,他在紐約市初選的勝利——距離9/11事件後伊斯蘭恐懼症的狂熱爆發不到25年——為人們帶來了一絲希望,即政治話語能夠改變,而且改變得相當快。例如,在加薩種族滅絕之前,僅憑馬姆達尼對以色列的看法,就足以讓他失去在美國政壇的資格。
歸根究底,如果選民不認為馬姆達尼是一位貨真價實的紐約人,他就不可能獲勝。然而,馬姆達尼並沒有刻意將自己塑造成一位傳統紐約民主黨人的漫畫形象,而是選擇運用自己的政治魅力,以一種能夠充分發揮自身優勢的方式重新定義這一角色——這場賭博似乎獲得了成功。
儘管印度複雜的選舉制度、極端的不平等、基於種姓的投票制度以及日益專制的多數制國家使得類似的故事幾乎不可能發生,但馬姆達尼對印度政治話語的貢獻可以讓我們理解,即使是那些被視為永恆不變的身份,也可以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更加包容,而這種演變最好由被排斥的人自己來引領。
Sarayu Pani 是一名受過訓練的律師,在 X@sarayupani 上發布。
《缺失的環節》是她關於影響印度的事件的社會方面的專欄文章。
The Wire 現已登陸 WhatsApp。關注我們的頻道,獲取最新動態的犀利分析和觀點。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
注意:只有此網誌的成員可以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