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民粹主義,尋找民主黨的指路明燈
快問快答:當代民主黨人在製定當前的政治和政策方針時,最依賴哪位政治思想家?呃…
我可以列舉曾經指導民主黨的理論家,很可能是四位英美「J」之一:約翰·斯圖亞特·密爾、約翰·杜威、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和約翰·羅爾斯。這四位理論家奠定了自由、平等、多元的自由主義社會的基礎,其核心是個人權利、政策實驗、強有力的國家幹預以及對國家經濟利益的基本承諾。他們的思想共同支撐著民主黨及其勞工盟友的政治哲學和政策綱領,這些政黨和盟友從20世紀30年代初到70年代憑藉“新自由主義”崛起並佔據主導地位,將個人自由與代表美國工人階級的經濟行動相結合。
我在20世紀80年代成長,我的政治立場也經歷了轉變:從高中時期在南方挨家挨戶為老布什拉票,到二十多歲時為克林頓做同樣的事情,再到2016年支持伯尼·桑德斯,如今則基本保持獨立立場。這種轉變的根源在於閱讀和思考這四位傑出的自由主義哲學家。對羅爾斯及其批評者的研究對我影響最為深遠,因為他提出的「政治自由主義」理念為公平規則提供了最強有力的辯護,這些規則允許人們按照自己的意願生活和信仰,同時尊重彼此的差異,並輔以基本的經濟保障措施,以防止社會經濟失衡。社群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對羅爾斯的批評不無道理,尤其是在家庭或教會等塑造人生的機構的核心地位以及國家主導經濟活動的愚蠢性方面。然而,羅爾斯式的自由主義,憑藉其對價值多元主義和基本福利國家的堅持,似乎更適合在像美國這樣多元化的國家中實現相對的政治和諧。
二十世紀的「核心中間派」自由主義,鑑於當時的經濟和社會結構以及我們在海外面臨的安全挑戰,提供了一種最明智的政治路徑。然而不幸的是,如今這種路徑卻被視為天真、失敗或無可救藥的懷舊。當從左翼到中間派都自稱是羅斯福式的民主黨人時,那麼他那具有歷史意義的總統任期及其戰後發展所秉持的理念和政治思想,便已失去了部分意義或鋒芒。
在現代,我真的無法說是誰或什麼在指導美國的民主黨人。
過去二十年間,某種形式的後現代反殖民認同政治(主要在大學校園內)以及一套完整的民主社會主義和反資本主義理論,逐漸在民主黨精英階層中佔據主導地位。黨內大多數進步派活動人士對任何與早期自由主義相關的內容都置之不理或予以譴責,除了對個人權利的模糊承諾之外,他們主要的理由是“新自由主義”或“第三條道路的自由主義”未能有效應對美國社會日益加劇的不平等,並導致工人階級選民逐漸脫離羅斯福和杜魯門時期以勞工為導向的民主黨。
川普的崛起和全球右翼民粹主義的興起進一步擾亂了民主黨的理論思維,因為該黨領導人和戰略家們仍在尋找某種難以捉摸的人物、社交媒體聲音或靈丹妙藥般的信息來“順應時代”,並將人們團結在一個不確定的未來願景之下,而這個願景唯一的聯繫就是“不是川普”。
拜登領導下的民主黨試圖建立以綠色產業政策和「中產階級經濟學」為基礎的治理模式,但無論從政治層面或政策層面來看,都遭到了選民的斷然拒絕。一小群反壟斷人士提出了一些打破經濟權力集中的好點子,這與自由主義者早期挑戰企業「巨頭」的努力不謀而合。同樣,左翼民粹主義者在反對派中也取得了一些成功,他們抨擊富人,並最近大力推廣「可負擔性」作為民主黨政治的總體框架。但說實話,這些左派的努力大多只是在情感上迎合那些對現代生活感到迷茫的年輕人,在許多情況下,他們的這種看法不無道理。這些努力與一些過時的政策掛鉤,例如政府經營的雜貨店和紐約市當選市長佐蘭·馬姆達尼提出的凍結租金政策。就目前而言,這種模式對於生活在政治競爭不激烈、教育水平高、生活成本高的城市環境之外的工人階級和農村選民來說,並不能引起他們的共鳴,也無法成為國家政治或經濟成長的模式。
同樣,源自黨內中心和眾多新聞界「思想領袖」的「富足」運動,擁有一套切實可行的理念,旨在清除官僚主義的桎梏,確保政府在基礎設施、能源、住房、交通和教育方面的支出切實有效,改善美國中產階級和工薪階層的生活。然而,坦白說,這些概念過於抽象,與渴望擁有充足就業機會、廉價能源和物質商品的工薪階層的日常生活和願望幾乎毫無關聯。富足主義的中間路線提出了許多重要的建議,有助於改善政府運作,尤其是在那些數十年來設置重重監管障礙阻礙建設和發展的深藍州和地方政府。但這並非大多數黨內領導人所認同的政治願景,也未獲得大量選民的廣泛支持,許多選民已經退出了該黨。
在現代民主黨人的思想鬥爭中,是右翼民粹主義和川普的個人崇拜模式,與不受約束的文化和經濟左翼主義、聲名狼藉的新自由主義,以及尚未確定的左翼民粹主義和富裕主義的結合體之間的較量。
如果這聽起來令人困惑,那確實如此。你不難理解,為什麼川普式的民粹主義儘管存在局限性,卻能對抗左翼和中左翼的替代方案:一方有明確的領袖人物,其綱領清晰明確,旨在限制移民,並通過減稅和放鬆監管來“釋放”美國主導的經濟增長;而另一方則沒有領袖,沒有變革理論,也沒有政策共識。
政治哲學無法解決民主黨內部的緊張局勢和理論上的混亂,尤其是在未來十年選舉繼續在兩黨之間交替的情況下。但是,認真反思上文提到的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自由主義偉人的思想,將對該黨大有裨益,或許經過一些更新,還能使其對自身目標有更清晰的認識。
一個有吸引力的政治黨派需要一個連貫的框架來獲取和運用權力,以及一套基本理念和更詳細的政策來實現這一目標。
羅爾斯在這方面或許能提供極大的幫助。在羅爾斯的「政治自由主義」世界裡,人們被視為成熟的公民,他們被要求彼此體諒,並努力在不同的見解和思想背景下找到共存之道。 (不再有文化戰爭。)任何人都不會因為種族、性別或宗教信仰而受到虐待或歧視。 (不再有身分政治。)人們是自由平等的公民,任何人都可以憑藉自己的智慧和抱負在生活中取得成功。人們擁有財產,國家不像社會主義國家那樣控制經濟。此外,還有一套完善的社會福利體系,以確保人們不會陷入困境或絕望的經濟境地,從而阻礙他們在生活中取得有意義的進步。 (以成長和再分配、減少貧窮以及縮小收入和財富差距為重點的混合經濟模式。)
這就是我們所知的西方自由民主,它既有中間偏左的一方,也有中間偏右的一方,也是上個世紀民主黨政治和政府成功的基礎。
它或許並不新穎,但它或許可以作為捍衛自由、平等、經濟成長和國家利益的行動的理論架構。
關於此帖的討論
約翰,這是一篇很有見地的文章,我同意你的核心擔憂,民主黨缺乏一個人們能夠看到和信任的連貫框架。
我想補充一點,單靠政治哲學是不夠的。執政黨也需要一種方法來思考制度在良好運作狀態下的實際運作機制。在政治領域之外,有兩位思想家對我的這方面幫助很大,他們是戴維·漢納和W·愛德華茲·戴明。
漢娜的觀點直截了當卻又要求很高:只有當制度的目標清晰、合法且被受影響的人所接受時,它才能有效運作。如果民主黨人信奉幹預主義政府,那麼他們就必須在目標上格外嚴謹,不僅要有良好的意願,更要製定出人們能夠理解並認可的合理目標。
戴明提出了另一個我認為超越意識形態的視角。他認為,工作重組顯示系統上游的某些環節出了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講,龐大或不斷增長的社會福利支出不應被解讀為道德上的成敗,而應被視為其他系統(工作、住房、教育、醫療保健)未能發揮應有作用的證據。
目前的一個例子是國會就增加醫療保健補貼問題所展開的持續爭論。無論最終結果如何,這場辯論的持續本身就是一種改進。它揭示了更廣泛的醫療保健體係以及奧巴馬醫改結構的一些重要問題,這些問題需要後續的改進和改進。然而,這場辯論幾乎總是被定義為道德問題,而其根源卻是系統設計問題。
許多人對看似無止盡的返工感到反感。他們或許不會用「無止盡」這個詞,但他們覺得這套系統並沒有解決根本問題。除非民主黨人能夠更好地識別返工背後的含義,並重新設計系統以減少返工,否則他們將繼續在廣大選民中難以獲得認可。
羅爾斯提供了一個強而有力的道德框架。漢娜和戴明則幫助我們理解如何使任何框架在實踐中真正發揮作用。
今天的共和黨恰好更接近政治光譜的中間位置,而這個光譜由於自稱民主社會主義者和非常左傾的 80/20 政策聲明(這些聲明更多的是被嘲笑而不是被認真對待)而向中間偏左的方向發展。
1960 年代末 1970 年代初,在校園激進抗議和城市騷亂期間,20 多歲的民主左派——至少那些沒有倒戈到另一邊的人——如今已是上了年紀的退休人員,年紀大了,但智慧卻絲毫未增;思想膚淺,精力也更加衰弱。
政治真空確實存在,但幾乎沒有什麼「免費的東西」可以填補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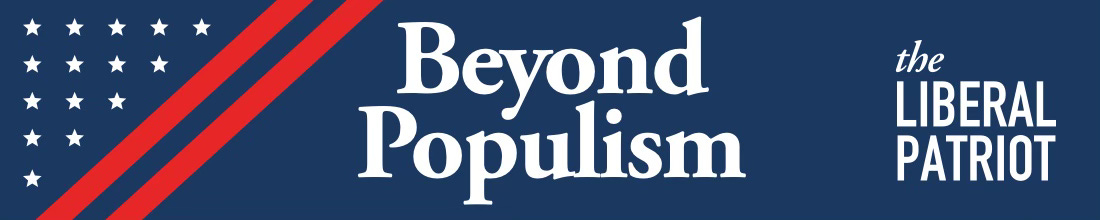



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