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71 998 312
- khaiminhbook@gmail.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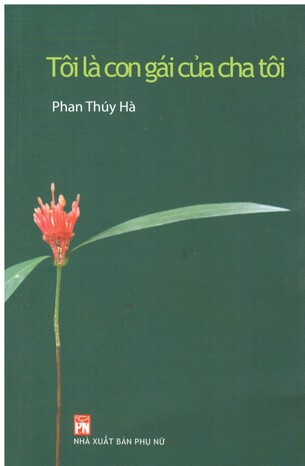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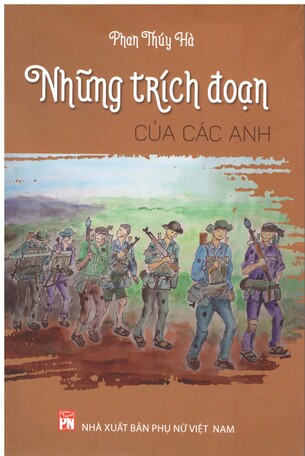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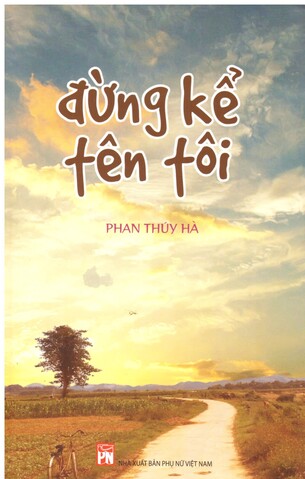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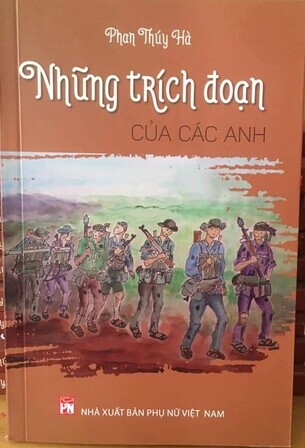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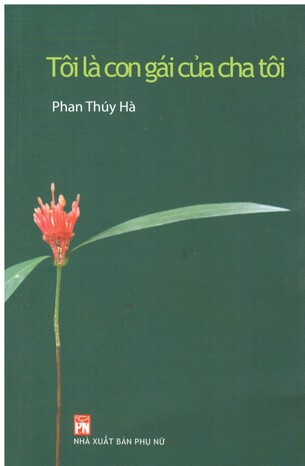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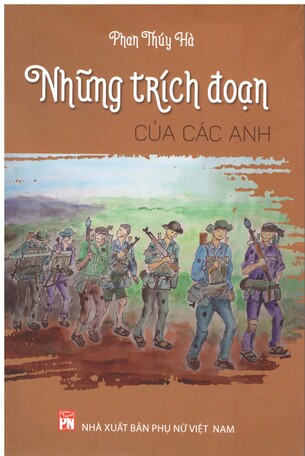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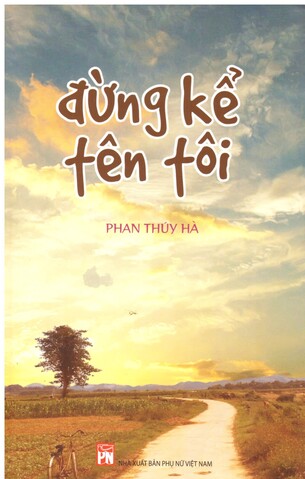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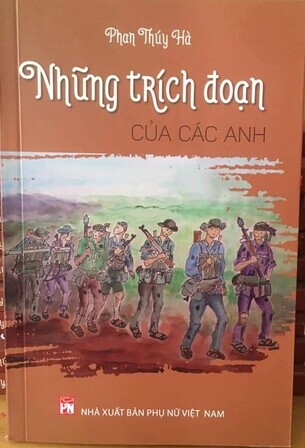
傷口/越南的不幸
吳氏金菊
(閱讀潘翠哈的兩本書《別告訴我的名字》和《我是我父親的女兒》)
這是一位出生於1979年的作家在越戰停火四年後寫的《越戰概要》。
至今,沒有人知道這兩個地區究竟有多少士兵陣亡,以及有多少平民遭到「交火」/故意殺害。潘水哈無法見到在戰鬥中犧牲的將士,也沒有機會見到高級將領。她只能和普通士兵見面,聽他們講述戰爭年代的青春歲月,並記錄…
那些零散的、顫抖的、充滿淚水的碎片,跨越了空間和時間,跨越了二十多年的敵友界限,連接在一起,突然展現出那場消耗了人類太多筆墨、造成了太多爭議、分裂,直到現在——在它結束四十四年後——仍然有太多問題沒有得到解答的戰爭的畫像。
或許潘水夏自己也沒有完全明白自己為何要承擔這個任務,但最終她卻做了一件自己從未想到的事情:為那些再也沒有回來的士兵/孝子們寫一篇悼詞,或者說,為他們在戰場上留下的一份骨肉/寶貴的青春再寫一篇悼詞。這是一段經歷,是一次巨大的損失,士兵們永遠不會忘記,永遠不會停止思考,直到生命的盡頭。
無論在北方或南方,每個士兵的戰爭歷程都是不同的。有些人為了理想而自願參戰,有些人則是被迫無奈參戰。但他們上戰場的時候,是直接拿槍的人,會殺人,也會被殺。他們同樣感受到了士兵所面臨的悲劇。在戰場上,人的生命在炸彈和子彈面前毫無意義。在那裡,親人、故土遠在天邊,愛情無處可尋,只有戰友與你共享死亡與無意義……戰場的真相太過殘酷。死亡是如此簡單,像一個笑話,像一種諷刺,像一種懲罰…
《別告訴我的名字》(婦女出版社,2017 年 12 月)中的我是從北方離開的士兵。在那片土地上,人們只能透過美國飛機的轟鳴聲、炸彈的轟鳴聲、傷者的哭喊聲或親人死去後生者的尖叫聲來感知戰爭。
有懷抱偉大理想出發的戰士。而在家裡,他們卻餓著肚子來支付軍隊的糧食。戰場上,他們常常餓著肚子作戰,但他們仍然是甘願犧牲的勇敢戰士,因為他們從小就懷抱著深深的仇恨。
……我在流動影院把電影《阮文卓》看了十三遍……我把卓伊說的每句話都背下來了……晚上,我夢見卓伊站在槍桿子前,卻依然義正辭嚴地說著話……要是能像卓伊一樣死去該有多好啊……我明白了為什麼我的祖國遭受如此多的轟炸,為什麼美國人要對我們人民犯下罪行。美國人佔領了南方,美國人還會進攻北方。越南將被美國人吞併。美國人將統治這個國家。越南人民將陷入漫漫長夜…”
缺糧挨餓,是各家的事。共同責任還是要履行的。每個年滿十八歲的公民,每年必須向國防繳納十公斤生豬肉。如果沒有豬肉,就折算成六十公斤米……公民有義務供養軍隊。從軍隊拿一粒鹽,都是叛徒…」。
有些人帶著不同的心態去參戰。有些人二十歲了,一顆子彈都沒開,也沒見過「敵人」的臉,就毫無意義地死去了。
「… 許多來自 Cam Xuyen 的林業工人被徵召參軍。
十五天的訓練框架......想像一下,十五天你能學到什麼?安仍然不知道如何拿槍......緊急命令前往廣治增兵。 1972年4月12日下午,我們出發了…下午5點,我們被命令今晚渡過石漢江。 「向老闆報告,我不會游泳。」酋長拔出了槍。 「這是戰鬥命令。如果你不會游泳,一個三人小組會把你拉過來。」將救生衣充氣,放入背包和隨身物品並繫緊。抓住救生圈。與你的隊友保持一致。來到溪流中間。大水。密集叢生的水葫蘆。河面很寬。河對岸,大砲和機關槍轟擊不斷。我猶豫了。掙扎著 Luong 絕望地呼救。點頭。我到達了另一邊。屍體漂流到了越國…」。
如果和平能為士兵帶來他們所夢想的一切,那麼士兵在戰爭中所忍受的一切都將變成值得驕傲的回憶。失去的青春/身體部位、戰友的死亡……都沒有白白浪費。然而,就在最後勝利者的故土上,卻存在著折磨、疑問和深深的悲傷…
……我身上沒有傷,一次也沒中過槍。退伍前最後一次體檢,身體一切正常。回鄉幾年,身體漸漸衰弱,四十三歲,犁地拉車都乾不了了。家裡的主要經濟支柱落到了我老婆身上。她累得不行,說,十二年了,總該有薪水了。
我在戰爭中學到了什麼?我學會了忍耐。我學會了看待事物並看到這一切都會過去。一切都會過去。妻子累得不行了,再也抱怨不了什麼,孩子們也陸續有了工作。我現在可以死了...」。
……後來我才知道,部隊把我列為烈士了。還好他們還沒給我家鄉發訃聞……我回到部隊,制服被沒收了。藏在背包底部四年多的筆記本也被沒收了……我回到部隊,繼續接受前往西原作戰富勒羅的任務……1976年底,我獲準回鄉。我已經在戰場上離家五年了……菜園荒蕪,房子空蕩蕩的,破敗不堪。妹妹去北方學手藝了,只有年邁體弱的母親一人生活……我怎能拋下母親?我入伍,辦理了退伍手續。回家後,我砍竹子、茅草,在菜園裡挖土,重建房屋,幫助母親維持生計…
……我剛剛讀了你的信。她給我寄了一封信,寄到她母親在鄉下的地址。
深夜,看到兒子平安回到家,母親安然入睡。我打開了每一封信。我的眼淚流下來了…
……我的青春,沒有人奪走我的青春……」。
這是一個多次死裡逃生的戰士受傷的心靈發出的痛苦的呼喊。他參加了佔領西貢的軍隊,體會到了初次接觸西貢人民/街道的北方農民的感受。有那麼多的疑慮、警惕、驚訝、困惑……年輕的士兵不敢回應這位充滿信任的西貢女孩的感情,因為有那麼多的恐懼和偏見……直到他真正明白,一切都太晚了……
勝利者如此,失敗者又如何呢?
在《我是我父親的女兒》(婦女出版社,2019年第三季)中,我是作者-一個北方士兵的女兒,也是一個1975年後不得不去「再教育營」的南方士兵的女兒。
南方士兵的肖像畫風格多樣,細節豐富,蘊含著無數殘酷的戰爭/戰後真相。因為南方士兵以自己的眼睛看待戰爭,以平民的身份了解戰爭,所以他們中的許多人都試圖逃避兵役。
當他們無法逃脫時,他們就不得不發動戰爭,而作為失敗者,他們必須為那些成功逃脫的人付出代價。
他是一名下士,1973年因失去一條腿而退伍,但1975年後他仍然必須去再教育營,原因無人能解釋。
……我長大後,看到父親兩排牙齒只剩下四顆。他說是因為營養不良,而且他讀書多年,牙齒都掉了不少……我父親從解放前到2013年一直沒有公民身分。 2013年,父親病得很重,眼看就要死了。我去幫他辦了身分證……我想讓他在去世前也能像其他人一樣成為公民。我跟他們說:給我父親一張出生證明,讓他去辦死亡證明。答應幫忙的人說:唉,他不辦還能怎麼辦?
這名傷兵不僅失去了雙腿,後來還雙眼失明,並患有冠狀動脈狹窄、肺癌、腰椎退化、泌尿道癌等。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天,上帝賜給他一個奇蹟,讓他再次見到了那位曾與他分享過一段不幸的愛情、一段無法經受戰爭考驗的愛情的美妙女人。
他也是河內本地人,他的家人擁有一家經營河內-海防路線的巴士公司,1954年他只有一歲時就移民到了越南。在被徵召入伍之前,他與一群無家可歸的青少年一起在隆城倉庫附近的美國垃圾場度過了童年…
……美國人出現了,社會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水泥橋修建起來,高速公路通車……妓女們出現了,為美軍士兵服務……鄉村姑娘們離開田地,到酒吧和夜總會尋歡作樂,直到最後都為了取悅美軍士兵。我從未見過越南婦女的尊嚴受到如此的貶抑和羞辱。在自家門前,女人們或站或坐,互相談論著如何讓自己看起來更光鮮亮麗。然後她們放聲大笑,比較著黑人和白人的身材……我當時只有十六歲,坐在那裡,她們毫不在意。她們的丈夫在戰場上…一個男人回來後,在妻子生下一個白人孩子時開槍打死了她…如果我是你,我不確定我會做出什麼不同的舉動…
這名士兵歷經千辛萬苦,分配了一份工作給自己…
……那時,我在教會上電腦維修課,閒暇時也上網,後來還學會了設立臉書。有一天,我走在街上,遇見一位聽起來境況悲慘的殘障老兵。我問了他原單位的名字和電話號碼,然後拍了一張照片發到臉書上。沒想到,有人看到了,紛紛轉發,並藉此互相打聽……有人請我幫忙給照片或影片裡的人轉帳五百、一百萬……漸漸地,很多人知道了我的所作所為。他們聽說有一位殘障老兵,就傳簡訊給我。我循著地址找到他,確認訊息。一份小小的禮物,一句小小的問候,雖然無法改變一個生命,卻能溫暖弟兄們的心。
他也是一名傷殘軍人,1961年入伍,1970年在廣南受傷,一生十分悲慘:
「……地板上鋪著一張破爛的舊墊子,一個人影躺在上面。一隻胳膊斷到了肩膀。兩條腿也斷到了腹股溝。一條短褲遮住了它。襯衫磨損了,紐扣斷了,一個紐扣縫在另一個紐扣上。”
妻子說:我賺錢養家已經很辛苦了,還要鼓勵他、照顧他。他只想死。
那棟房子裡沒有什麼叫做財富的東西。這個飯碗也是他太太用來盛裝橡膠乳膠的碗。幾把塑膠湯匙。幾個凹陷的鋁鍋。吃飯的時候,她會拌一碗飯和湯餵給我。他咀嚼併吞嚥…
……最後一張照片是李叔叔臥病在床,蓋著一條皺巴巴的毛巾。他躺著的地方附近有一個窗框。他就那樣躺著,度過了每個清晨、每個下午,幾個月、幾年。他一生的三分之二時間都這樣躺著…
為什麼還要活著?因為醫生已經盡力搶救他了。因為四十八年來,他的賢慧妻子一天也沒有離開過他…」。
在南方,遭受災難的不僅是那些持有槍支的人。當手無寸鐵、陷入交火時,最悲慘的受害者是人民。任何一方的槍都有殺死他們的權力。白天是民族主義者,晚上是共產主義者。在那些農村,人們不知道該如何生活,死亡分分秒秒都在向他們襲來。
在廣治省 Cam Lo 地區,有一戶人家的丈夫去了集結地,也就是奔海河對岸。隨後,丈夫試圖返回,尋求家人的支持,而他的妻子則成為所有逮捕和審訊的對象。
……被集中到北方的家人都被列入了黑名單。每年都會有幾次清洗。區保全會把所有人都趕到村里,家人之間互相指責。犯了輕罪的坐在一個角落裡,犯了重罪的坐在另一個角落……每次清洗,母親和妻子都會被帶走審訊。每次這些人裡,總有一個母親。有時只有一個人被叫走。這個人就是母親。
等她回來的時候,臉色已經黑得像煤炭一樣。母親觸電了。它們電擊了她的指尖,她跳了起來,然後又跌倒在椅子上。
……從1966年仲夏到1973年初,母親遭受了無數次的折磨。他們將肥皂水和辣椒混合,倒在我的臉、鼻子和喉嚨上。讓媽媽坦白
丈夫在哪裡?越共在哪裡?秘密掩體在哪裡?多次為越共提供米飯......
……母親的十根手指因觸電而終身抽筋。
她背部的皮膚正在流血。臀部一側潰爛,有蛆蟲。釋放後,臀部已壞死。母親因此終身殘疾。她的屁股是歪的,她的背是歪的,她的腳步是歪向一邊的…」。
以下是另一名士兵的自白:
……孩子,太可怕了。我不想再提戰爭了。在戰場上,戰死沙場還好,但在村落裡,人命關天。人命比雞還不如……叫你去渡口,你就得去。第二天早上,渡口上就堆滿了死屍。沒有判決,沒有審判……我表哥四十歲了,還得去當兵。他去的時候,有人勸他回來當老百姓。他開小差,又回來,幾天後就被槍殺了,不知道是誰開的槍……誰受不了,就跳進森林裡。他們不喜歡進森林,就跳進軍隊裡…”
……他指著左手臂上的一處傷口。那是他開槍自殺的地方。他心想,死了也就算了,但如果手臂斷了或失去了,回家後該如何活下去?戰爭從未結束。自殘是會被判入獄的,但連長都替他掩護。後來,他像連長一樣,也開槍自殺了。他負了傷,逃走被列為二級殘疾士兵,然後退伍。他痊癒後,繼續前進。
繼續下去,直到你失去一條腿和一隻眼睛。
1973年,在廣治省的石漢江上,一名18歲的傘兵被一顆子彈擊中,子彈從他的背部射向腹部,刺穿了他的膀胱和尿道。傷口太大,必須等肉長出來後才能進行手術。 1975年4月,這位20歲的戰爭傷殘軍人艱難地回到了家鄉檳椥,高興地想著自己可以治癒傷病,過上平民生活。此後他又多次存錢去西貢找醫生,但西貢的醫生都已經走了。他回來了,並接受了帶著尿袋度過餘生的命運。
他在田野裡搭了一間小屋,靠養鴨子維生。在他二十七歲的時候,他的母親為他娶了同一個村莊的一位健康、勤奮的姑娘。她對未來丈夫唯一的印象就是他很英俊,而且很溫柔。
成為妻子的第一天,她驚恐地看到一堆電線纏繞在丈夫的胃上,旁邊還有一袋尿液。而且他們不能像其他夫妻一樣進行性生活。她隱瞞了真相,告訴親戚們,由於他不育,所以他們沒有孩子。她的父母都是佛教徒,每天都念經,祈求佛祖保佑女婿的病早日康復。她作為妻子生活了三十六年,她的丈夫也忍受了四十六年…
「……這房子是用舊鴨舍改建的。它被稱為房子,但實際上是一個有水泥柱子和石棉屋頂的棚屋。
停下摩托車,走進去,一股刺鼻的牛糞味撲鼻而來……外屋裡擺著她的茶几和床;內室、牛棚和他的床。
… 一間棚屋裡住著兩個人和四頭牛。或者換句話說,那個牛棚裡住著兩個人。
我簡直不敢相信我所看到的東西是真實的。我想尖叫。為什麼要這樣生活?
我已經習慣了。這兩個字解釋了我所有的沮喪。
……他提醒我喝椰子水。我的心很亂。我看著那杯椰子水。我看著他身邊那個深黃色的水袋…
……她從很遠的地方送我走。我痛苦地看著她。那你從來沒有這樣做過?她搖了搖頭。這時我才看到她的眼淚。淚水順著她的臉頰滾落下來,她趕緊擦乾了眼淚。
……我開了幾十公里,過了無數座橋才得以停下來。我把臉埋在雙手裡。我抽泣起來。他的話語很柔和。 “如果你晚一點放出來,也許他就沒事了。”
另一名士兵曾擔任海軍陸戰隊員、偵察兵、虎騎兵,他的傳記中充滿了戰鬥/行動故事。太多生命已經逝去,人類用盡各種方法造成死亡…
他講述了戰爭結束的那一天:
……失去了三分之一的胳膊,三分之一的右腿。我的左手還剩下三根手指。我的傷口在阮志方醫院治療。阮志方醫院撤離時,傷口還沒有癒合……在維新綜合醫院待了一個星期後,峴港也淪陷了。醫生和護士都離開了……沒有人照顧我的傷口。我餓極了……我爬到一個倉庫,想找兩支拐杖。我四處張望,每個房間都擠滿了傷員……從倉庫裡出來幾個傷員,手裡拿著藥品。一個傷兵看到我爬得那麼慘,就讓我坐在那裡,自己進倉庫找拐杖。
我把兩根拐杖夾在腋下,出了醫院。
我不習慣用拐杖,走幾十步就得休息一下。一名受傷的士兵躺在人行道上。腿上打著石膏,但傷口是開放的,所以醫生切掉了一塊石膏來照顧傷口。無論他爬到哪裡,都會掉出蛆。新傷口若在二十四小時內不加以處理就會壞死…」。
作為一名前童子軍,他記得蛙人課程中的教訓:
當你感到疲憊或挫敗時,不要垂頭喪氣。盡量抬起頭並微笑。
「……偵察兵的知識和技能幫助了我行軍…
……1994年,牧師聽說我以前參與過童子軍活動,於是他來找我商討開設童子軍部隊的事。我認為自己是殘疾人,我怎麼能做到這一點?但我也想嘗試一下。 …我真心愛孩子。我小心翼翼地引導著它們……慢慢地靠近。有一次,他們看到我拍手肘,他們也拍手回應。我笑道,不要模仿 Truong,因為 Truong 沒有手,所以他才會那樣拍手。他們笑著,他們喜歡像酋長一樣拍手…
…… 1995年,一位朋友送給我一台電腦。我練習用剩下的三根手指打字。我充滿激情地寫作。寫作幫助我忘記悲傷。當我寫作時,我又找到了自我。
《野外生存》和《通用職業技能》是我喜歡的兩本書。這兩本書都是我以軍人的心寫的。
….我的妻子剛過四十就過世了。去年我的兒子在一場車禍中喪生。我代兒子養兩個孫子,大的二年級,小的上幼稚園。孩子的母親正在學習一門手藝以便能夠養活自己。
……我仍然每天上網學習英語。我仍然印書,透過寫書、賣書賺錢。
我累了嗎?答案永遠是:我不累。 」
參加戰爭的那一代就是這樣。他們的孩子怎麼樣?
一位年幼的女兒寫給在再教育營的父親的信。那個小女孩,描繪了1975年後南方社會不幸的心靈畫像中的一小小一角。
峴港。 1975年5月20日
親愛的爸爸
今天我有空,寫幾句話詢問您的健康狀況。我聽媽媽說爸爸去挑水砍柴了,我好愛爸爸啊,現在媽媽要是讓我去跟爸爸一起住,幫爸爸挑水砍柴的話,我一定會立刻答應的。那裡常下雨嗎?媽媽去跳蚤市場買斗篷,但沒有。爸爸,盡量保持健康,爸爸。砍柴和挑水會讓你很快生病。哦,你的胃痛好些了嗎?如果你進入森林,你可能會感染瘧疾,如果你感到寒冷,你又沒有毯子可以蓋住自己。
… 停止 !由於蚊子叮咬次數過多,爸爸要我停止寫作。
我的兒子」。
「峴港 6-26-75
……我聽媽媽說她會在 30 號去探望爸爸,所以我馬上寫信給你。
爸爸,昨天黃老師要我帶你去參加六年級的入學考試。你帶我去「Co Man」學校參加數學和作文考試。我數學試卷做完後,檢查了2-3遍才提交(爸爸,我先提交的)。至於作文測試,我描述了「課間休息時的校園」。當我提交我的論文時,Phuong 先生看了看,然後把它交給 Huynh 先生看,然後他向全班讀了我的論文。他告訴我媽媽,我有文學天賦,我是最優秀的,他會給我一張證書,讓我申請弘德大學。但是現在我家很窮,所以我根本不想去上學,因為書和筆很貴,爸爸......我想在公交車站賣水賺點錢,但是那裡有很多其他孩子在賣,但他們賣得不好,因為那裡太擁擠了......」。
“1975年12月25日
…爸爸,那裡冷嗎?在這裡,我們早上都懶得刷牙。晚上我們睡覺時會蓋著毯子,裡面再蓋一層衣服,但我們還是抖得厲害……爸爸,你上面有毯子嗎?可以帶一個給爸爸嗎?快到春節了,爸爸卻不在家,真是難過……有時候,我和媽媽都會想像爸爸回家的情景。我和媽媽馬上就待在家裡了。媽媽沒有去上學,我們也不再去上學了…現在,如果我能有一位仙女,她會滿足我的三個願望:家裡會有足夠的食物和飲料來慶祝春節,我們會有很多新東西,爸爸會回來。我會選最後一個。
*
戰爭和人性的殘酷並不能阻止人們同情一顆真誠正直的心,儘管它被無情地粉碎了。
Phan Thuy Ha 自費出版了她的書,因為她想知道誰在購買/閱讀她的書。
《別告訴我的名字》這本書在南方受到許多讀者的購買。潘水河「聯絡」這些讀者前往南方。他們會把她介紹給可以接待她/和她交談的人,這樣她就可以寫第二卷。
“我們的生活殘酷得難以言表,但你們為什麼要受這麼多苦呢?你們是自願去的。”
許多南方老兵在讀到《別告訴我的名字》時,回想起北方士兵講述戰場故事的那一刻,他們在哪裡,在參加什麼樣的戰鬥…
……1971年5月底,南寮戰役結束……醫護人員把我抬上一輛開往北方的客車……我躺在車上,凍得瑟瑟發抖,時而清醒,時而昏迷。我是唯一一個瘧疾患者,其他十個人都受了重傷。大家都躺著,沒人能坐起來。偶爾會傳來痛苦的尖叫聲……一枚炸彈在山邊爆炸。石塊和泥土落進客車,砸在車上躺在地上的人身上。又是一陣尖叫聲……第二天早上,我們被擔架抬進一個大山洞……我們在那裡待了一天,目睹了十五次轟炸。每次炸彈落下,山上的石塊都會像石灰一樣白地落進山洞裡…”
「……白天學政治,晚上就餓,餓到骨子裡,餓到骨子裡……總想著怎麼弄點吃的……標準是每人每天四兩米。沒有蔬菜,沒有糧食,沒有鹽。四兩米的標準已經不復存在了……我們到森林裡去尋找、咀嚼各種植物和樹葉,看看有沒有可以吃的東西……」
「……瘧疾患者的標準是每週一餐鹹魚,一湯匙湯。從柬埔寨運到前線的鹹魚已經變成了乾魚,散發著難聞的氣味。我神誌願人起不來床,我們希望一碗撒著芝麻鹽的熱米飯……衛兵們散發著難聞的氣味。我神誌起不來床,我們希望一碗撒著芝麻鹽的熱米飯……衛兵們餓得要命,炊事員起不來床,我們希望一碗撒著芝麻鹽的熱米飯……衛兵們總是餓得要命,炊事員起不來床,我們希望一碗能上來敵人……」
……這是我第三次受重傷,不得不住院三個月。出院後,被派去檢查站時,我走路都走不穩了……高峰期,白天陽光明媚,溫暖舒適,但夜晚卻冷得刺骨。每個人都穿著一套撕碎的長袖衣服,沒有毯子,也沒有蚊帳。坐在檢查站,我緊張不安,食不下嚥,睡不著覺,神經緊繃得像吉他弦。炊事員送來的飯菜,只有一個人吃。山腳下,敵人有步兵。山上每隔十五分鐘就響起砲彈,炸彈毫無規律地落下……我叫兄弟們把剩下的米飯晾乾……晚上,一群老鼠來吃米飯。我設下陷阱,抓了十幾隻大老鼠……老鼠被烤了、宰了、切了塊,用油煎了……兄弟們興奮地坐在那裡等著享用……第二天一早早上,我出去查看哨所。 Binh和Tri站在哨所裡說:“我們聞到人肉的惡臭了……我順著倒下的茅草路走,看到很多老鼠屎。旁邊還有五具屍體,頭骨露了出來……老鼠的痕跡還清晰可見……是新的……”
士兵離開軍隊返回後方的故事:
……文件?我全都丟了。把屍體抬回來……他給我看了看他的手。手掌粗糙,感染了……這隻手收過多少屍體?我不知道。我做了三年……部隊指派每個人把三、五具遺骸送到師公墓。一年前、兩個月前、一個月前,甚至十五天前的墳墓……把它們挖出來。撿起來。一把匕首。還有兩隻手。把肉都剝掉。把骨頭帶走。從早到晚幹……他們的名字? ……去B點之前,士兵被告知不要帶地址。如果幸運的話,趁還能說話的時候問問他們的名字。至於沿途犧牲的重傷員,屍體是在戰場上撿到的……他們的名字是匿名的……”
……在我離開之前,有妻子和女兒。 1976年,我回國,身心俱殘。她流產了三次。第四次,她生下一個沒有嘴巴的孩子。孩子出生一天後就死了,好讓她的父母免於痛苦。第五次,她生下一個孩子,少了一根手指或一根腳趾。
……在我們村,我叔叔是服役時間最長的,總共十五年。他從1960年離開,直到1975年底才回來……1964年,他去了廣治、承天順化。 1967年,他去了西原。他在西原待了很久,掌握了當地少數民族的語言,也養成了不少當地居民的習慣。新來的士兵叫他“老鄉”,請他教他們巴拿語和埃德語……十二年杳無音信。村裡的人都以為他死了。他走的時候,母親還健在,回來的時候,雙眼失明,再也見不到兒子了。他站著、坐著,任由母親隨意按摩他的手腳,撫摸他的臉和肩膀……她確信兒子還活著,哭了起來。她哭得像在夢裡見到了兒子,生怕夢醒了,兒子就此消失……”
三天三夜,他都在回答同一個問題:為什麼他還活著,還能回到這裡?這時他才知道,當時和他一起去的戰友們,大多都死了。其中一個去了阿羅伊,打了兩場仗,他嚇得不得不回去。部隊派人到他家逼他回去。他回去打了一個月,然後就死了。
– 這十年間,你有沒有想過叛逃?
- 是的。五十、六十名槍手組成的陣型向前衝去,等回頭一看,只剩下三、四個了。想回家但怎麼回家?遵循聯絡路線並獲得曝光。到處閒逛迷路也會害死你。我寧願和我的戰友們一起死在這裡…”
……我們剛從戰場回來,是國家的恩人,必須身體健康才能回後方工作。三個月後,醫生來幫我們檢查,看我們還很虛弱,就安慰我們,說必須身體健康才能回後方工作。還登廣告說有些部門需要人手。過了一會兒,他們又來給我們檢查,看我們身體健康了,就直接說:現在你們要繼續執行任務。我們的任務:拿著槍。拿著槍!繼續拿著槍!我們是普通人,沒有什麼大夢想,只想回家工作,正常地生活…”
*
有人讀了潘翠霞的《我是我父親的女兒》後對她說:“以前她如果這樣寫,可能會被抓起來……”
這個人無法理解哈在創作這本書時的想法和經驗…
當時,河某到一位越南共和國退伍軍人的家中詢問情況,妻子很怕丈夫提起“政治問題”,只想趕走這個陌生的北方姑娘。
最後…
……是的,我突然這樣,心裡很亂。我說話很快,因為我怕姑姑會趕我走,這樣我們就沒有機會了。叔叔,你知道嗎,你是我現實生活中遇到的第一個敵人。以前,我只透過電影、書籍、報紙、網路上的文章,以及在網路上聽過你。今天我這麼近距離地看到你了。我強忍著沒說完話,眼裡噙滿了淚水。我擁抱了叔叔,告別了。他也回抱了我。這讓姑姑和她的女兒們都驚呆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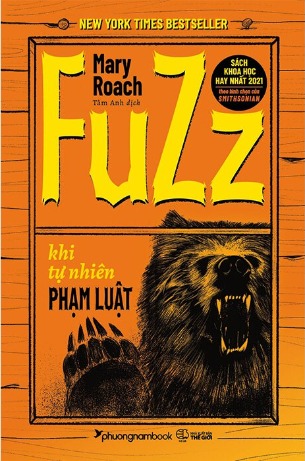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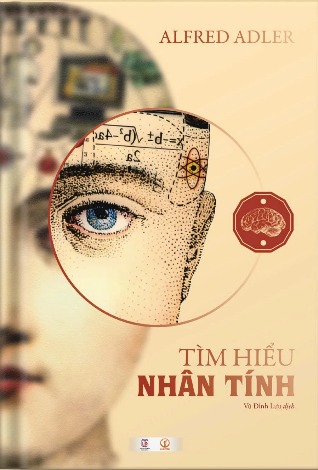
![[特別版] 宗教社會學導論 - 楊玉勇博士](https://bizweb.dktcdn.net/100/180/408/products/226-2.png?v=1715667466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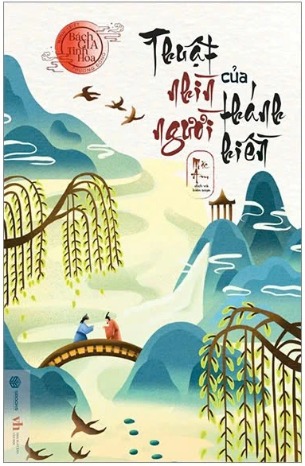
![宗教生活的原始形式 [精裝] (Les Formes Élémentaires de la Vie Religieuse) 埃米爾·塗爾幹 (Émile Durkheim)](https://bizweb.dktcdn.net/100/180/408/products/nhung-hinh-thai-so-nguyen-copy.jpg?v=1734943026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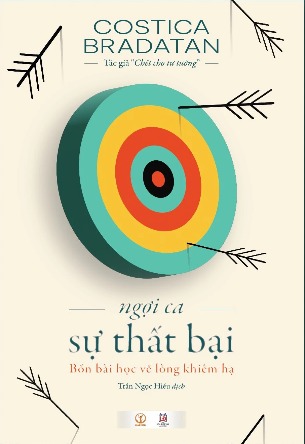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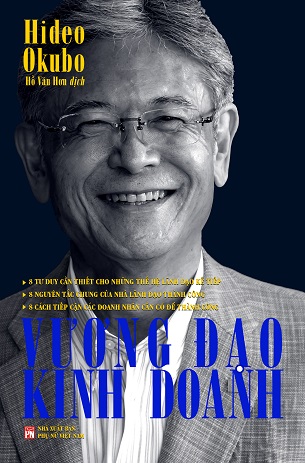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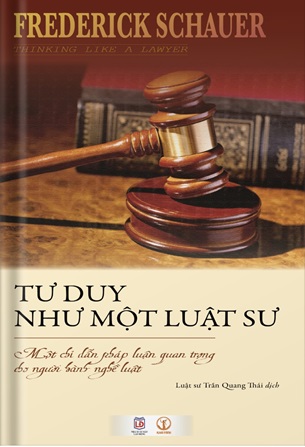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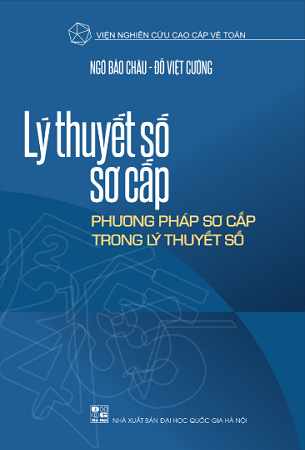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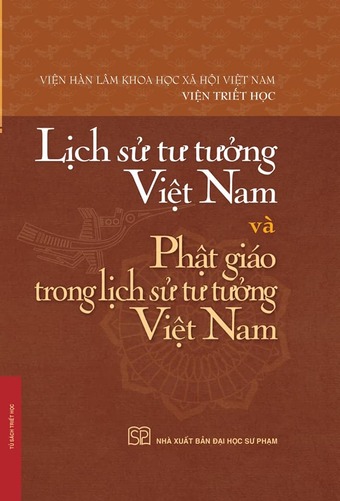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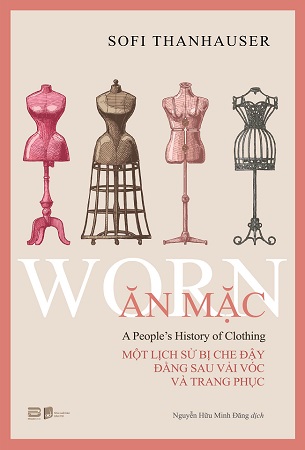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
注意:只有此網誌的成員可以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