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在都是對著牆壁跳舞的人了
Afra的新節目《 Coulwa Been at the Club》和Lauren Teixeira剛剛在播客上發布了關於 CHINAMAXXING 的內容。點這裡收聽。
下面我們還刊登了Afra對劉怡玲的訪問。
GovAI成立於十年前,其創立的初衷是相信人工智慧最終將改變我們的世界。十年後的今天,該組織始終走在行業前沿,致力於幫助政府和行業的決策者順利過渡到先進的人工智慧時代。
GovAI 現正招募下一批研究學者和研究員。研究學者職位為期一年,旨在為雄心勃勃的研究人員和政策專業人士提供一個學術平台,幫助他們提升職業發展或轉型進入人工智慧政策領域。研究員職位則是針對經驗豐富、成就卓越的研究人員,為他們提供一個能夠支持其最具影響力研究工作的平台。
這兩個職位都提供了相當大的自由度,可以進行政策研究、為決策者提供建議或發起新措施。
申請截止日期為2026 年 2 月 15 日。如欲了解更多資訊並申請,請造訪https://www.governance.ai/opportunities 。
如果說有一本書我期待已久,那一定是這本:《牆舞者:在中國互聯網上尋找自由與聯結》,作者是劉怡玲,她既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榜樣。書中講述了一位中國企業家經營全球最大的同性戀交友應用,並曾與李克強總理(已故)握手的故事。書中也描寫了GitHub如何在新冠疫情審查期間成為資訊避風港。此外,書中也探討了TikTok的快速發展及其困境:這家全球性公司既因雄心壯志的實現而受益,又因地緣政治的變遷而飽受批評。
如果說易玲的作品有什麼共同的主題,那就是它們總是回歸到中國的技術與政治參與。長期以來,人們普遍認為中國的網路是個異類;中國的網路是一座監獄,而不是我們曾經被承諾的自由、平等、光明的網路!然而到了2026年,這種論調已經過時了。我們如今身處的網路和科技世界,其內在邏輯和最終目標越來越接近中國,而不是相反。看看美國公司TikTok是如何審查內容的,這對中國網路使用者來說早已是司空見慣的手段。
西方早已失去了對科技的純真,直到最近才意識到,它必須向中國網友學習一些經驗:如何在演算法時代,在科技巨頭的掌控下尋求自由和連結。這本書的出版可謂恰逢其時。
以下是劉怡玲與阿芙拉就她即將出版的新書《牆舞者:在中國網路上尋找自由與連結》的對話。 您可以透過此連結訂購本書。
下面我們聊了一下:
戴著鐐銬跳舞:本書的核心隱喻
選擇舞者:為什麼這五個角色體現了中國互聯網的演變
創作之道:如何透過人的故事讓中國網路鮮活起來
方與守:開與閉的循環
這場舞蹈還能繼續嗎?人工智慧時代的科技與行動主義
人際交往的表面積正在縮小
「中國崛起時刻」揭示了美國的哪些問題?讀者應該從中領悟:中國並非鐵板一塊,每個人都必須找到屬於自己的真相。
戴著鐐銬跳舞:本書的核心隱喻
阿芙拉:你的書名為《牆上的舞者》——每次看到這個書名,我都依然為之著迷。你沒有選擇「鬥士」、「創新者」或「異議者」這樣的詞,而是用了一個更巧妙、更含蓄的詞語來指那些在中國轉型過程中游刃有餘的人們。中國既是世界上最大的網路使用者群體,也是人口最多的威權國家之一。你稱他們為「舞者」。這個字捕捉到的不是苦澀或反抗,而是更接近真實的質感──喜悅和捉迷藏般的樂趣。人們巧妙地躲避審查,當你看到一個精妙的政治梗圖毫髮無損地溜過審查時,那種恍然大悟的瞬間。在那一刻,有一種心靈的交流:我了解你,你也了解我。你是舞者,我也是。
那麼,是什麼讓您選擇「舞者」作為您書中主角的身份象徵呢?這個比喻又是如何體現您所說的「國家與社會之間動態的拉鋸戰」的呢?
易玲:謝謝你指出了這個詞中蘊含的喜悅和活力——這正是它吸引我的地方。 「在枷鎖中起舞」(dài zhe liàokào tiàowǔ )這個短語最早出現在2000年代初期,當時中國記者用它來描述在國家約束下進行報道的感受。此後,它迅速傳播開來:音樂家們用它命名了一首歌,劉慈欣(中國最著名的科幻作家,《三體》的作者)在《三體》的前言中引用了它,軟體工程師們也開始使用它。它完美地詮釋了生活在中國就意味著參與到一種深刻的動態之中──在自由與控制、壓制與解放之間劇烈搖擺。
舞蹈需要敏捷和靈活。我筆下的人物必須應對不斷變化的環境,所以我稱他們為「牆舞者」——他們擅長在中國互聯網乃至更廣泛的中國公共生活中,在一個邊界不斷變化的體制內,爭取尊嚴和人際關係。

選擇舞者:為什麼這五個角色體現了中國互聯網的演變
阿芙拉:那張移動牆的圖景真是太貼切了。任何上網的人都知道,它不是一動也不動的磚牆──它會追逐你,時而消失,時而又重新出現。牆本身在跳舞。
我們來聊聊你的舞者們。這本書圍繞著四位主要人物展開:馬寶利,中國最大的同性戀交友軟體Blued的創始人;呂品,中國知名女權主義活動家;胡卡菲,四川地下說唱歌手;陳秋帆,科幻小說作家,前谷歌員工;以及第五位人物,劉埃里克,他像徵著微博審查員——防火牆本身。他們分別代表了中國互聯網的不同層面:馬寶利代表創業抱負,呂品代表女權主義覺醒,胡卡菲代表藝術鋒芒,陳秋帆代表精英科技工作者,而劉埃里克則代表防火牆本身。為什麼選擇這些層面?你有沒有考慮過其他舞者,但最後沒有選擇他們?
易玲:有很多。我考慮過環保運動和勞工權益運動的參與者——這兩個群體都需要各自複雜的策略。但我更想關注邊緣群體、地下群體和底層群體。那裡才是最具想像的策略得以萌芽的地方。
關鍵在於,這些人雖然身處邊緣,卻懂得如何在主流社會中運作。馬寶利曾是中國警察,是名副其實的「內部人士」。呂志剛曾是官方記者。陳志剛在一家大型科技公司工作。就連饒舌歌手胡卡菲也在中國經營普通的生意。這種遊走於內外之間的能力,使他們既理想主義又務實。他們能夠靈活切換身份,戴上不同的面具。例如,馬寶利憑藉其警察背景,能夠用權威的語言說話,這對他日後的生存至關重要。
將他們聯繫在一起的另一點是,我們有著共同的個人經驗。在創作和寫作受到限制、難以找到自身定位的過程中,我開始接觸嘻哈音樂人。在努力接受自己能否公開戀愛的現實時,我開始尋求酷兒社群的幫助。疫情期間,我聯繫了女權主義活動家,因為我想了解在封鎖狀態下,團結究竟意味著什麼。他們的故事與我探索如何起舞的歷程交織在一起。
阿芙拉:我喜歡這種說法:生活在防火長城之內的人都在不斷地問自己,我該如何行動?就連胡錫進這樣的人——這位民族主義小報《環球時報》的前總編輯,這位臭名昭著的大嘴巴、擁有2.5億微博粉絲的親政府網紅——都可能被封禁(事實上,他已於2024年被封禁)。每個人都在跳舞。
創作之道:如何透過人的故事讓中國網路鮮活起來
阿芙拉:我們來聊聊寫作技巧吧。讀你的書,我感覺自己彷彿穿越回了過去,置身於你筆下人物的內心世界。這種沉浸感源自於你精雕細琢的筆觸──因為在你的文字裡,每個角色、每個場景、每個時代,以及那些難以用語言表達的氛圍,都躍然紙上,栩栩如生。這種沉浸感,這種穿越時空的體驗,彌足珍貴。
舉個例子,當我讀到馬寶力發現北京同志(一位筆名的同性戀作家,他1998年出版的小說成為一代中國酷兒男性的精神支柱)的網絡小說《北京故事》時,他徹夜難眠地讀完,那一刻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我感覺自己彷彿身臨其境。當女權運動家呂萍辭職時,她說:“我是八九一代”,我立刻就認出了她。這句話正是呂萍會說的。你捕捉到了她的神韻。
你是如何將這麼多細節串連起來的?你是如何蒐集這些一手資料的?你撰寫如此龐大專案的過程是怎麼樣的?
易玲:在著手撰寫本書的任何主題之前,我都會花上幾個月甚至幾年的時間研究他們的世界,並撰寫相關文章。因此,我帶著豐富的背景知識去做這些訪談。例如,在2018-2019年,我對同性戀交友軟體Blued產生了興趣,並想為《紐約時報雜誌》撰寫一篇關於它的文章。但他拒絕接受訪問。於是,我效仿了美國傳奇記者、新新聞主義先驅蓋伊·特立斯(Gay Talese )的做法——當年弗蘭克·辛納屈拒絕接受採訪時,我採訪了所有與他關係密切的人:Blued的員工、LGBTQ+社區成員、投資人等等。一年後,在那篇文章發表之後,我再次聯絡他,希望為本書撰寫訪談內容。他同意了。我認為,所有這些背景調查工作都至關重要。
這些人大多是半公眾人物,他們在網路、社群媒體和影片中分享了自己的故事。沒有人將這些零散的訊息串連成一個連貫的故事。我並非在做調查新聞報道,挖掘獨家新聞。我只是把分散的片段重新組合,賦予它們生命和色彩。
馬友友發現《北京故事》的那場戲?他用兩句話就講過幾百遍了。每次聽,我都會想:如果把那場戲完整地重現會是什麼樣子?於是我讓他一遍遍地給我描述。網咖在哪裡?你坐哪兒?你旁邊那個女孩是誰?你什麼時候離開的?補充這些細節,讓場景鮮活起來。
然後是更宏大的架構——將個人故事融入中國網路發展演變的宏大敘事中。我採訪了各領域的數十人。僅就嘻哈音樂而言,除了Kafe Hu之外,我還採訪了至少十幾位藝術家,以及了解這個行業的把關人。我用一個龐大的谷歌表格記錄了所有人的資訊。最耗時的部分在於如何用情感和視覺上的細節,將他們的故事生動地呈現出來。
阿芙拉:哪些時刻給你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易玲:太多了。關於馬,有一個他很少提及的夢:晚年時,他反覆做著同一個夢,夢見自己回到了警局,卻找不到自己的辦公室。這個夢深深地觸動了我──那種紮根於某個角色和地方,然後又被連根拔起,不知自己是誰的感覺。
胡卡菲決定搬去成都,這深深觸動了我。任何一個年輕人說“我受夠了這個小鎮,我要去城市追逐夢想”,都是普世的渴望。
阿芙拉:有些瞬間或許能概括整整一代人的懷舊之情:馬雲會見李克強總理,握手,獲得國家對Blued的支持。現在回想起來,就像一個時光膠囊,讓人難以置信這些事竟然真的發生在中國。就像央視那些關於LGBTQ組織在各地成立的片段一樣,永遠消失了。
方與守:開與閉的循環
阿芙拉:這正好引出了我的下一個問題。中國網路的早期階段——充滿活力、混亂又繁榮——即使對我們這些親身經歷過的人來說,也感覺像是上輩子的事了。但這與西方的情況很相似。二十年前,我們對科技的願景要樂觀得多。我在Dweb Camp期間見過蒂姆·伯納斯-李兩次,每次我們討論到如今的局面時,他都說,當初設計萬維網協議時,他從未預料到會是現在這樣的結果。
您寫到中國開放與收緊的週期性模式,但指出這次的轉變發生在全球技術轉型的大背景下——從早期自由開放的萬維網,到如今封閉、孤立、商品化的萬維網。我們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
易玲:我會盡量言簡意賅,但需要說明的是,我沒有完整的答案。歷史的變幻莫測難以預測。
或許真正的問題在於,我們天真地接受了這種目的論式的發展軌跡──科技等於解放──並將其視為必然。比爾·柯林頓曾說控制網路就像“把果凍釘在牆上”,如今看來幾乎有些滑稽。自由與控制、去中心化與中心化之間的張力始終存在。而我們才是能夠推動這種張力回歸民主化和解放方向的人。
從中國視角來看,這種「開放與收緊」的循環貫穿了整個現代史。文化大革命的鎮壓之後是改革開放;自由奔放的八十年代末期以天安門事件告終;2013年的微博之春——那場思想的繁榮——之後便是收緊。當體制開放過快,動搖了國家政權時,當局就會重新加強控制;而當控制過於僵化時,改革的壓力就會不斷累積。
中國與科技創業家的關係完美地詮釋了這一點。 2010年代中期充滿活力-字節跳動成立,創投湧入生態系統,黨鼓勵創業者大膽創新。然而到了2020-2021年:馬雲的螞蟻集團IPO被叫停,大型科技公司遭到打壓,以及「全民共榮」運動的推行。儘管人工智慧領域出現了一些微小的開放跡象,但我們仍然處於這種封閉週期。
但這正值全球威權主義轉型的大背景下。 2008年的金融危機讓許多人對西方自由化感到失望。 「阿拉伯之春」的失敗讓各國政權意識到,數位工具不僅能用於革命,還能用於鎮壓。史諾登2013年揭露的美國國家安全局監控行為,粉碎了人們對科技與自由關係的幻想。而2016年——川普當選、英國脫歐——則證明,即使在民主國家,社群媒體也可能被操縱影響輿論。
因此,我們看到中國國內的管控收緊是全球威權主義轉向大趨勢的一部分,兩者相互映照。所謂的「自由」網路和防火長城背後的網路也開始變得相似,趨於融合。
這場舞蹈還能繼續嗎?人工智慧時代的科技與行動主義
阿芙拉:你的書中很大一部分探討了科技如何重塑社會運動——微博之春、女權運動、#MeToo運動(它偽裝成“米兔”,這個諧音詞讓這場運動得以繞過審查)、白皮書抗議等等。即使監控手法日益複雜,人們仍能找到新的方式來表達異議。例如打「界外球」(乒乓球術語,指在規則邊緣擊球),甚至創造新的詞彙來規避審查。就我個人而言,我的第一個中文播客節目《Loud Murmurs》正是在那個時代誕生的。那段經歷讓我和我的伴侶清晰地意識到身為女性的意義,意識到在複雜的網路環境中互動意味著什麼,以及如何發出我們自己的聲音。
在人工智慧時代,這種局面還能持續下去嗎?當像小紅書這樣的平台上的演算法旨在馴服和安撫用戶時,我們該如何保留異議的空間?
易玲:我既樂觀又悲觀。一方面,新科技出現時,會經歷一個蓬勃發展的階段──去中心化、創造力、人們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使用它。這為創新、異議和各種可能性提供了可能。
另一方面,我曾與一些中國新創公司創辦人以及人工智慧實驗室的研究人員交流過,他們指出人工智慧平台是建立在網路之上的。如果網路平臺本身就已經是資訊孤島且中心化的,那麼在這個基礎設施上建構人工智慧,就像在位元組跳動的地基上建造大樓一樣,意味著權力仍然集中在少數人手中。人工智慧能否像90年代末期的網路一樣,創造出同樣的反抗空間與活力?我對此表示懷疑。
但我相信一般人的創造力和獨創性。即使是“直覺編碼”,這種對系統進行實驗性改造的方式,如果人們能以掌權者意想不到的方式進行創新,也可能很有前景。
真正具有顛覆性(儘管這種顛覆性令人感到悲哀)的,其實就是獨立思考的能力。擁有不受演算法塑造的自我意識——這本身就是一種深刻的顛覆行為。
人際交往的表面積正在縮小
阿芙拉:我一直在思考那種逐漸增強的孤獨感,以及我們與他人建立聯繫的管道是如何隨著時間而不斷減少的。早期的中國網路上,有那種聊天室,五百個陌生人聚集在那裡,沒有特定的話題,只是彼此好奇:你是河北人?我是廣東人!我們相隔那麼遠,卻能聊天──你好嗎?你的生活怎麼樣?那種渴望連結的心情。
後來,網路逐漸演變成僅與親朋好友聯繫的工具。微信和Instagram變得越來越私密。如今,我們甚至開始與聊天機器人對話。我認為,集體政治行動——抗議、社會活動——需要對他人的好奇心、同情心和相互依賴。如果你和我一樣遭受苦難,我們就是同志。我們是一個社群。但人工智慧縮小了這種交流的範圍。公共的不滿變成了私人的,被引導到人工智慧的對話中。
我也擔心個人主義的盛行。人工智慧賦予了人們極大的自主權——設計師不再需要產品經理或工程師,產品經理可以脫離設計師或工程師獨立工作,而工程師則渴望繞過他們。每個人都在用人工智慧取代彼此。
易玲:太慘了。你所描述的這種狀況——人們彼此失去聯繫,失去漢娜·阿倫特所說的“常識”,甚至失去與彼此身體的聯繫。她說孤獨是極權主義的根源。當你與他人失去聯繫時,控制就變得更容易。
「中國崛起時刻」揭示了美國的一些問題
阿芙拉:咱們換個更貼合時代精神的話題:「中國時刻」。到了2025年,西方年輕人開始自稱中國人,宣稱“我正在瘋狂追捧中國”,“這是我人生中非常中國化的時刻”。更別提TikTok用戶湧入小紅書,Labubu爆紅網絡,以及中國在人工智慧領域的成就。很多人都在認真討論,這是否就是中國的世紀。
您的書追溯了中國互聯網三十年的發展。經過這麼多的報道,您的看法是什麼?我們是否正在步入中國世紀?這對您書中的舞者和核心主題又意味著什麼?
易玲:很高興你問這個問題,因為這個問題一直被一再提起。這是一種相對較新的現象,是在我完成這本書之後才出現的,所以我一直在思考這其中的連結。
郭凱撒寫了《大清算》,之後你又寫了《與中國的另一次清算》,路易絲·馬察基斯和楊澤義在《連線》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關於中國市場擴張的精彩文章。轉捩點可能是去年一月,小紅書的TikTok用戶流失,以及DeepSeek的發布。這一切始於矽谷科技精英們的「閒聊圈」——他們前往中國進行為期兩週的旅行,回來後驚嘆不已:「我坐了一輛華為車,車裡到處都是螢幕!」「那些跳舞的機器人!」「高鐵!」如今,隨著哈桑·皮克和約翰尼·索馬裡等網紅訪問中國,這種現象正逐漸進入主流文化意識。
但關鍵在於:這種論調並非針對中國,而是針對美國。我在中國的朋友說,他們的生活並沒有在2025年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這完全是美國人視角的轉變。
中國已成為美國人投射自身恐懼與慾望的一面鏡子。過去,人們的敘事是「中國是一個我們無法忍受的糟糕地方」——妖魔化。如今,敘事顛倒過來,變成了「中國是一個完美的烏托邦」——理想化。美國執著於自身的功能失調,以及自身基礎建設的無能。美國人終於意識到,中國幾十年來一直在建造橋樑和建築。
Gary Zhexi Zhang寫了一篇文章,完美地詮釋了這一點:
新東方主義與以往不同;美國人發現,大洋彼岸的異域帝國或許與我們有很多相似之處——一個以增長為目標、靠殘羹剩飯為生、辛勤勞作的技術資本主義社會——只不過他們的操作系統似乎運作良好,至少相比之下是如此。
從純粹的物質產出來看——電動車、人形機器人、橋樑、TikTok和Temu等網路產品在全球擴張——我們是否正在步入「中國世紀」?或許如此。但對我來說,更清晰的是,我們正在步入「美國式屈辱世紀」。
拋開種種預測,中美兩國的網路其實驚人地相似。我們目睹了非自由主義聲音的崛起、公共領域的萎縮、常識的喪失──彼此之間的連結正逐漸消失。我們看到權力日益集中,政治領袖和企業執行長掌控著數位空間,攫取我們的注意力以擴大影響力。在中國,科技公司執行長和黨政長期以來一直沆瀣一氣。而現在,矽谷幾乎全員都在向川普政府卑躬屈膝。
直到讀完這本書,我才完全領悟到一點:美國人也必須學會像跳舞的人一樣對著牆壁跳舞。
阿芙拉:這很有深度。當他們討論如何欺騙X演算法以避免被限流,當他們對TikTok的審查制度感到恐慌時,這已經展現出舞者特有的那種能量了。
你對美國痴迷中國的描述讓我想起了我在中國長大時,美國就像一座不切實際的燈塔,承載著無數的希望和憧憬。中國人真的關心美國人的日常生活嗎?不。他們被美國人對未來的憧憬、高等學府、自由主義、自由精神和個人英雄主義所吸引。正是美國塑造了馬寶利世代——創業世代,並為中國如今的活力做出了巨大貢獻。
我認為大多數美國人對中國「熱潮」並不真正關心真實的中國。這讓我想起賈樟柯的電影——那些超現實的場景,例如UFO離開地球或機器人走過,但這些奇觀與主角的故事線毫無關聯。 UFO、機器人、高科技始終處於背景之中,與電影中的角色無關。我稱之為「酷中國」(被西方媒體誇大)的形象與真實的中國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而真實的中國依然如故。
易玲:沒錯。所以我對這波矽谷遊客訪華浪潮感到矛盾。如果他們的目的是深度參與、真正了解、對真實的中國充滿好奇——我完全贊成。但如果只是為了獲取一些膚淺的印象,比如“中國擅長建橋”,而忽略了歷史背景和更深層次的含義,那麼這些印象就會被過度解讀,最終淪為某些不知名文件中千篇一律的政策條文。
讀者應該從中領悟到:每個人都必須找到自己的真理。
阿芙拉:最後一個問題:在理想情況下,你希望讀者在讀完你的書後能獲得什麼有意義的收穫?
易玲:對於不了解中國文化的一般讀者來說:中國並非鐵板一塊。要了解這個地方,就要通過真實的人性故事。外在對中國的認知常被簡化為簡單的二元對立──要不是充滿無限機會的經濟巨頭,就是權力至上的威權國家,沒有人能自主選擇。我們在這兩種極端之間搖擺不定,忽略了人性的複雜性和矛盾性。而一個人的故事,恰恰能夠展現這種豐富性。
另一個重要的啟示是:每個人都能找到屬於自己的道路,正如瓦茨拉夫·哈維爾所說,「活在真理中」。每個人都能開闢出一片屬於自己的尊嚴、自由和正直的空間。這片空間或許很小,或許很大。但在日益複雜的科技系統中,找到屬於自己的生存之道至關重要。
阿芙拉:我們社區一直以來都在大喊「中國不是鐵板一塊!」。就像現在,在中國網友眼中,美國就是一個反烏托邦的鐵板一塊──槍枝氾濫、謀殺案頻傳、無家可歸、芬太尼成癮、醫療費用高昂。在美國,中產階級一旦生病,就會立刻墜入地獄。 ¹嗯,我也想對著那些沉迷於末日論調的中國網友們喊:美國也不是鐵板一塊。
伊玲,謝謝你。這次談話讓我受益匪淺。
易玲:謝謝你,阿芙拉。我很榮幸你能如此認真地閱讀這本書。這次談話對我來說是一份禮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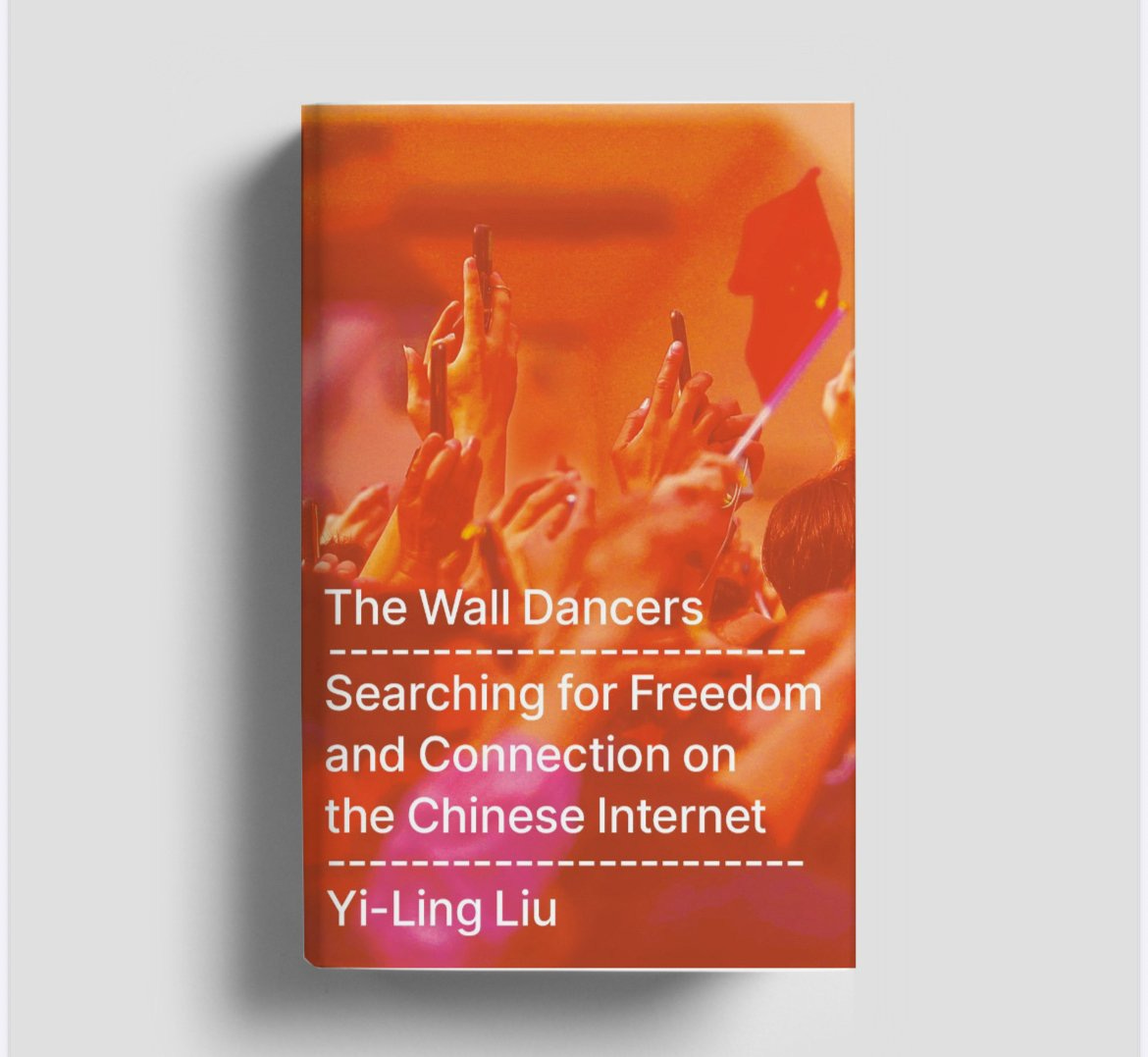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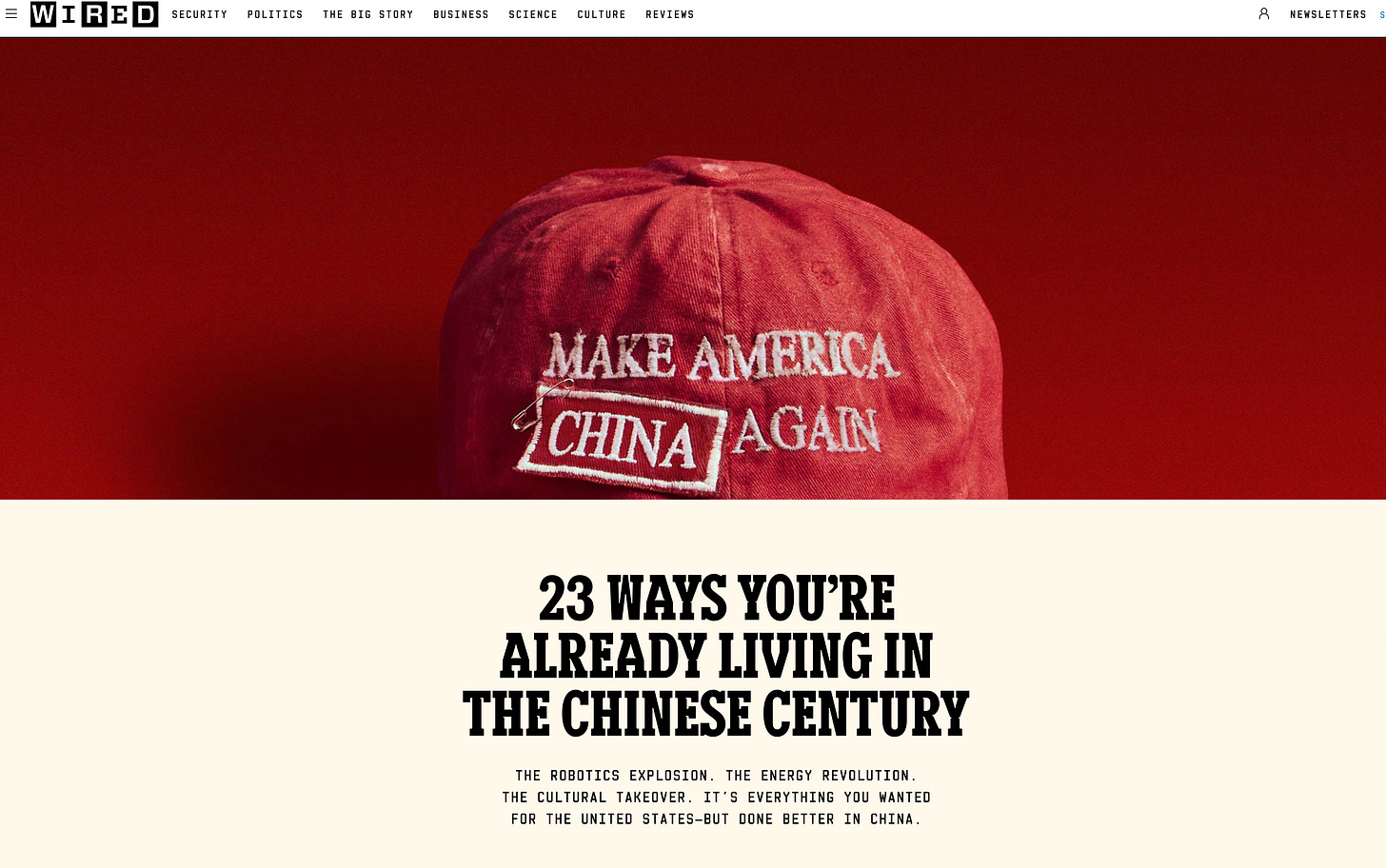
留言
張貼留言